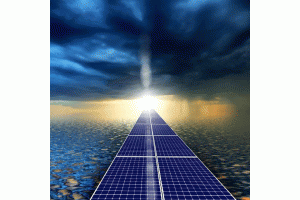能源轉型2020:不可預見的奇跡
綜合能源 vs 增量配網 vs 電力市場 vs 虛擬電廠
如果我們從戰略層面再下沉一點到達戰術層面來觀察,能源互聯網發展了四五年一直被大家詬病的就是覺得概念無法落地,似乎找不到什么抓手放量增長。這個事情其實非常像當年的互聯網,馬云馬化騰們大概用十年才摸索出了游戲、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等所謂入口,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能穿越到十年后看一眼,應該會看到抓手不外乎上面標題的某一種。
綜合能源是兩年來國網提的最多的戰術關鍵詞,2019開始成立了各地的省綜合能源公司,調集了不少主業的精干去開拓新的業務。但是綜合能源其實存在一個天生的邏輯矛盾就是:綜合能源絕不是電力公司所長,而是如浙能川能這樣名馬正宗的綜合能源公司的陣地。與很容易獲得營收的電力運營相比,今年100億哪怕是200億的綜合能源運營目標實在是太弱了,這就注定這一塊業務在決策層心中的地位隨時岌岌可危。
遇到同樣困難的是同樣在轉型的騰訊阿里們,他們從產業互聯網的另一頭趕來,花了巨大的代價也才創造了100億200億的云端收入,這和互聯網巨頭上千億的營收相比也是杯水車薪舉步維艱。
為什么在中國,銀行無法領頭做全和金融有關的所有業務,交通領域也無法地鐵巴士飛機三輪車綜合交通服務,但醫院就可以內外科婦產科骨科品類齊全,餐廳也可以湘菜粵菜簡餐西餐相得益彰?反過來,國外就醫先去專科診所,吃飯尋找意式法式,但交通運營都是套票一家,銀行提供證券理財咨詢審計綜合業務?
是否綜合,取決的不是甲方的意志,乙方的能力,第三方的建議,而是用戶心理。
因此以用戶為中心,是綜合能源的必由之路。但是現在的綜合能源業務,動輒談冷熱電三聯供冰蓄冷相變儲熱,又或者智能運維能效監測,不是說這些不重要,而實際上這些都只是用戶需要的需要。
一等的用戶體驗,是用戶按照供應商的想法去做,自己還很開心。
二等的用戶體驗,是用戶不說供應商已經做了。
三等的用戶體驗,是用戶說了供應商馬上就做。
四等的用戶體驗,是用戶說了供應商說不行,要這么這么做才行。
最差的用戶體驗,是用戶懶得說自己要什么......
用戶體驗是一件互相成就的事情,當年被龍永圖斷定絕對不會不逛街的中國女性,用手指證明了任何用戶習慣都可以被改變,有信心去改變用戶心理的公司,才是能把用戶放第一的公司。互聯網公司在技術、人才、政策、品牌甚至銷售渠道都不占優的情況下,竟然逆襲了很多產業,靠的就是清晰的用戶畫像、準確的用戶服務。
人們可以再賭一下物聯網時代或者To B端的企業級業務還是不是這樣的邏輯,但即使還可僥幸些時日,所有做綜合能源服務的公司都會遲早面臨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用戶自己。
電網公司的唯一優勢就是電力,還僅限于圍墻之外。在不少大用戶的圍墻內是如何裝配三級計量如何依照工業生產調度運維的,又有多少用戶在蒸汽、熱、冷方面有如何五花八門的要求,可能海爾寶鋼這些大企業的動力部門會更加擅長。事實上如果大型企業尤其是十億度電以上級別的用戶在綜合領域多以自我團隊運營的方式完成,那被逼入中小公司圈圍的綜合能源公司會更加頭疼如何發掘滿足用戶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因此在KPI的催逼之下先丟幾個多能站儲能站就是可想而見的唯一自救之法了。
綜合領域內另外一個誤區,就是那些體量還不夠大無法以投資開路的公司,但是又覺得開發一個綜合能源平臺號稱一下泛在接幾個設備或者光伏儲能進來看看覺得很高級,這個思路已經衍生到業界幾乎任何一個公司都號稱有這么一個平臺,蘇州東莞廣州各地的供電局都在立項,浙能三峽華電也在招標,新奧遠景協鑫林洋這些民營企業也在各大論壇上言必稱智慧能源云,就連一些裝裝電表賣賣路由器的小微工程公司也摩拳擦掌。
此般重復投資自說自話的景象,和20年前一窩蜂的自建局域網,10年前各地山寨智能水貨手機有什么區別?如果沒有淘寶天貓,現在每個百貨公司集團甚至超市和品牌專賣店,就必須自己花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搞這么一個網上云平臺——這也正是目前在國外發生的。
一個生態圈如何錯落有致井然有序,看的就是行業老大們的正能量。理論上來講,國網云、南網云甚至于數據中臺本來的用意,就是搭建一個需要巨大投入的底層服務平臺,統一標準統一規范和評價體系,以國網南網的超級信用為體系內外的創新小團隊賦能背書,讓他們去做用戶滿意的綜合能源服務,看到有好的苗子就收購或者推廣。這樣一來,如果三五個人都能在比如負荷預測算法上獨到創新,借助平臺的力量一下推到200多個地市去或者一下子對接所有的玻璃廠,這才是泛在和能源互聯網原本的精華所在啊。
如今的景象,更像是那個南轅北轍的富人:你看我車還有HPLC通訊,你看我這個車減排了2噸Co2頂上還要光伏。。。以前蘇洵寫六國論的時候就一語道破:茍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如果我們已經經歷了這么多互聯網的顛覆還對行業壁壘和地位迷之自信,那真的是死無葬身之地。
同樣陷入絕境的是增量配網的發展。本來在2016年改革之處,售電放開和增量放開被認為是兩個很實際的抓手,增量配網在發改委能源局一批二批三批四批超過400個試點區域,本來增量配電網放開是本輪電改最大亮點之一。其前景在于以配網為基礎,開展售電業務,可實現配售一體化;或進一步實現多能互補、能源綜合利用,獲取更多商業利益;單獨的配電價格核定將成為必然,通過這個方式可通過收取配電價格回收投資。
但現實已經不僅是骨感,而是功能都不全了。以第一個電網公司沒有控股的貴安新區配售的公司為例,除了貴州電網和地方政府,混合了中電國際、泰豪科技等國有民營企業,股東的實力和能力都非常強注冊資金15億,但即使是如此豪華的配置也和幾乎所有增量配網公司一樣并沒有進入真正的創新發展軌道,看上去和原來的區縣供電局沒有本質區別。
電網公司當年宣稱的“守土有責”是有作用力的,但這一戰術的成功是不是導致連續兩年來被統一降10%電價的戰略打擊的主要動因就不得而知了。袁崇煥殺毛文龍、張學良槍斃楊宇霆的時候都沒有錯,權威第一寸土不讓,但是否會繼而導致一個王朝覆滅就很難講了。聰明人會選擇開門揖盜,明白人會以退為進,只有焦慮的理工男才會一頭撞死在大殿的某一根柱子上。
平心而論,在強調規模效應的電力行業的當下,在已經有服務和技術領先態勢的電網運營模式之下,在制造業慢慢轉型經濟發展進入平穩期的下個十年,增量配網這個也有外國模式色彩的舶來品在中國的發展在眾多行業變革中最不樂觀,試點了這么久大多數人的精力也都是放在一些很基礎的事情上——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如果增量配網的試點無疾而終,引發更高層面的切割甚至實施徹底的資本上的化整為零,都是可以想象的反彈。
同樣艱難但是未來尚可看好的是電力市場,所有人都不會想到僅僅電改5年后,我們就走到了現貨市場的門口。果不其然,中國的電力市場又成功的發展出了中國特色,與美國的歐洲的都不太相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對于價格動蕩的不信任。
這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情。或有人操盤,或有人告狀,或有人仆街,大家都沒法接受。所以最可行的辦法,就是把規則弄得既復雜又纏繞,不僅價格變化的有序緩慢可控,關鍵時候還可正大光明的各種干預。
如果沒有一夜暴富的吸引,誰還會去Casino?如果沒有足夠量的Player玩家進入,誰還有必要去發明那么多賭具和規則?電力市場雖然沒有必要囂張到這樣的地步,但集中那么多優秀人才花巨大精力去作一些違背基本邏輯的精美怪物,應當是這個行業幾年來最通用的毛病所在吧。
但長期我還是對中國電力市場的發展看好,只要不斷有人進場參與,最終中國也一定會出現十幾個金融數學畢業的年輕人,年營收數十億代理幾百幾千用戶的含金量很高的公司。如果野心再大一點,從代理汽油購買走向代理汽車運營,虛擬電廠運營公司會更加來勁。
虛擬電廠的本意,就像虛擬銀行、虛擬電信運營商一樣,是一種典型的跨區域OTT過頂業務。在分布式能源盛行的今天和馬上就沒有補貼而是平價競爭上網的明天,不可能每個光伏儲能生物質電站都搞一批人做預測做交易,于是能把這些分散在各地發電設備綜合起來運營的平臺就是虛擬電廠。
虛擬電廠與智能微網的區別,就在于不受地域的傳統限制,而是在信息化的前提下在線上完成OT運營,它依賴于電力市場和背后完善的金融信用體系支撐。
互聯網公司在進軍出行、外賣、理財之前,也不知道原來這么多線下的設備、服務、產品可以被一夜之間在線上完成統一和對接。美團滴滴們的實質,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對外賣小哥專車司機和小微企業完成了基礎信息化。
理論上來講,金風天合們搞的新能源云光伏云,儲能電動車公司們搞的儲能云充電云,最終應該都要匯集到虛擬電廠的云,而這些云彼此的區分不應該是各自的生產廠商來一朵云,而是運營主體的不同即規模和收益期望的不
但是,這個但是作為本文最悲催的一個但是,要無奈的揭示出一個可悲的現實:虛擬電廠當下的發展,竟然是被作為電網的一個調度性工具維持安全供電和有序響應,更接近一套供應鏈管理信息系統,而不是開放給市場的一次商業模式創新。
與前面幾個概念不同的悲催命運相比,虛擬電廠本來是最有互聯網色彩,現在活生生地加入進去秒級感應、萬物互聯的物聯網標志尚可理解,但是把滴滴出行活生生地做成河北出租車智能管理系統,還號稱填補以前沒有出租車管理系統的空白,到底是贏還是輸?
如果十年前各省各市看到移動互聯網起來了紛紛招標出租車智慧云平臺,靜安區外賣餐廳EMS,人民網虛擬作家朋友圈,這才是滴滴美團們最大的敵人:用蠅頭小利降低創新力。
如果真的要僭越,何不妨換個概念?綜合能源、增量配網、電力市場都有它不得不實施國情特色的苦衷和委屈,但虛擬電廠已經不是殺雞取卵,而是掩耳盜鈴了。
2010 vs 2020 vs 2030 vs 2050
從2000年到2020,如果用20年的時間窗口來看待能源電力行業,自然是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最大的轉型變化,其他一切均在其次。但如果再持續30年到2050年,用50年的標尺來衡量,那就不一定了,很可能是去中心化的物聯網才是最大的變化。
靈活的數字化,分布式的新能源,優越的人工智能,云端的大數據,很有可能都是去中心的物聯網的實現路徑。沒有一個物的狀態不是用數據來表述,沒有一個物不在網用數字來聯接。互聯網以低階的狀態出現,不過是為了讓人感受到聯網的好處進而打造從更宏大的物聯網而已,到最后人類因為糟糕的記憶力和計算力會不會被拋棄也未可知。
基于這樣的目標,一家公司的戰略選擇只能是:要么利用已有的資源和能力成為這個物聯網的運營商獲取最大的成功,要么躲起來利用各種辦法做最后一個被顛覆的堡壘也可以。所以之所以能源互聯網當初先跳出來并且大家對電力行業和電網公司們寄予厚望,無非只是因為這個行業已有的數字化基礎和充盈的優秀人才不引領風騷實在可惜。
但近幾年尤其是2019年電網公司和行業所謂領先的乙方企業的表現來看,泛在電力物聯網原本是個契機,但竟然幾乎所有人依然把這場變革當做是一次EPC或者BOT的大工程,拉虎皮扯大旗只求云露均沾,示范項目只為空前絕后,甲方的行業影響力淪為行業亦步亦趨的唯一動力,乙方的實際行動力躍升為行業獻計獻策的最后造假力,百億設備千億投資,似乎鐵了心要把自己都變成物聯網時代最大的工程EPC公司,一個個大項目干到2030。
其實站在2020年的入口看未來十年能源行業的發展,特別像2010年左右在電信領域看移動互聯網的未來。如今國網和南網現在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設想,當初中國移動和電信都曾嘗試過,無論是投資十幾億的飛信平臺,還是含著金鑰匙出身的咪咕系列,就像國網想打造國網云和南網想推鼎信、電商平臺創新一樣,原則上講有數以億計的用戶資源隨時賦能,也無需花重金砸來關注度和信任感,但就是做不過微信和互聯網公司,而且是一敗涂地一觸即潰,為什么會這樣呢?
最真實的原因,其實不是什么沒有互聯網的基因,體制束縛人。而是因為凡是這種級別的創新,往往涉及到行業的生死攸關顛覆轉型,比拼到最后的往往就不再是優越感而是求生欲,因為到最后起勝負手作用的往往不是實力,而是那種——對未知的奇跡的期盼。
司馬光在點評長平秦趙之戰的時候曾經說到:秦國趙國對峙好幾年,趙國其實早就輸在了起跑線上,無兵可加無糧可調,戰略上的布局失當使得廉頗唯一能采用的戰術就是用最慢的速度讓趙軍失敗,最后趙王無法支撐下去否則趙國整個都要被拖垮,只能換上趙括令其出擊。趙括表面上看是一個失敗者,但其實他的軍隊包括整個趙國做這樣的調整都只是基于已經要失敗的基本面而賭一個未知的奇跡。
秦國何嘗不是如此,只是換上來的白起運氣更好,真的等來了未知的奇跡。歷史上很多時候重要的戰略轉變的操盤者,往往決策的時候依然非常艱難,但是他們往往有因為相信所以看見的信念,敢去賭一個未知的奇跡。但是又不能像拿破侖、項羽這樣的超強實力派過于篤定自己的能力,反而把其他人的求生欲逼出來使得對手更加有機會勝利。
電力等傳統行業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轉變:以前是行業甲方巨頭發包立項目,大家跟著吃肉做工程賣勞力唯馬首是瞻,以后是巨頭運營底層云服務大數據平臺提供接入,供應商們變成應用層的APP開發上無孔不入的服務用戶。這個虛擬存在的信息化數字化平臺,當然不是當年運營商們理解的飛信短信,而就是微信淘寶。所有人最應該轉變的思路,不再是甲方乙方項目工程,數據中臺應該服務的是小微自由創業者、電科院退休的博士之流,而不是數據中臺部服務檢修中心交易中心。
即使是去未來穿越過的人,也只能劇透至此了。這一模式未來十年毫無懸念,成百上千的供應商們無非是從站在巨人的褲襠下變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命運也無懸念。唯一有懸念的,就是這個大平臺是由誰來操盤?如同問退回2010年,移動能否干掉騰訊?
機會永遠是均等的,也沒有哪個對手是不能戰勝的。BAT華為小米們一樣不具備產業化的基因,可能比能用想像力模擬互聯網基因的傳統產業巨頭們還不具備產業能力。只能在無人區域馳騁的互聯網公司就像匈奴的騎兵一樣防起來是很頭疼,但是要他們攻城拔寨一個個項目搶占產業地盤,恐怕管理上和基因上面臨的問題更多——管十幾萬快遞小哥和管幾十萬985、211畢業生是完全的兩回事,不加資歷經驗人品只看能力業績還真的會掉坑。
2020年機會依然均等,但只看誰能更開放,開放,開放:互聯網這么多退休的億萬富豪,請幾個情懷還在的來當CIO如何?掛職鍛煉不要老是去新疆西藏,去滴滴頭條行不行?
這些微妙復雜的景象未必行業巨頭們沒有看破,無法讓他們下定決心的只是此刻是否已到All In的關鍵而已。
用一定的周期迭代去鍛煉隊伍并且逐步轉型,可能是老一輩企業家們堅信的最可與理想主義區分開來的落地措施。但實際上一個締造偉大的戰略有兩條必需遵守:第一是強戰略之下所有人都是為戰略服務的棋子,衛青霍去病出現只是必然。第二是強戰略一定會要用對手擅長的方式擊敗對手,比匈奴人更擅騎射,比互聯網人更會地推,比華為人還997,中華民族都可以的。
1000年前熙寧變法的時候也是各種糾結,司馬光責問說反正你不是殺富濟貧就是殺貧濟富,王安石想了半天反駁到:我們沒必要過多地關注方法論,而是一定要堅持目標變法革新下去就好,遼、西夏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都是半斤八兩而已,反正我就是覺得中國肯定比其他國家更容易統一,就看誰撐到最后。王安石變法之后60年北宋覆滅,但是誰又能證明沒有王安石60年后老趙家不會輸得更慘?
所有參與這場能源變革的人包括90后都會在2050年退出歷史舞臺,而接下來到2030這十年似乎至關重要,不僅僅是各種統計數字的增加,也會在這十年中突然迎來商業運營模式的巨變。對于處于已經是奇跡的2020的人們而言,邏輯上善良的希望只能如此:
盡最大的努力,賭一個未知的奇跡。如果沒有奇跡出現,那只是因為你的努力不是最大。◆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作者:廖宇 來源:角馬能源 責任編輯:jian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