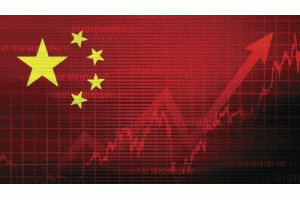深度觀察| 2019年中國經(jīng)濟展望:峰回,路轉(zhuǎn)
基本面二:中國主動去杠桿
在美國加息周期中主動去杠桿是為降低資產(chǎn)端風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興經(jīng)濟體(EM)出現(xiàn)過3次影響較大的經(jīng)濟及金融危機——80年代的拉美危機;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2015-2016年的資源型EM經(jīng)濟體危機。這三次危機共同的背景都是強勢美元影響,即當時發(fā)展最快新興市場突然出現(xiàn)資金流出和流動性急剎車。2015年底美國首次加息,一輪加息周期開啟。邏輯上來說,在加息周期中,可能受沖擊最大的莫過于高杠桿、高負債。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政策在2015年底的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提出“三去一降一補”是2016年主要任務。
從杠桿率數(shù)據(jù)看,中國宏觀杠桿率大致持平于發(fā)達國家均值水平。其中政府杠桿率偏低但非金融企業(yè)杠桿率偏高,這與體制特征有關,即部分國企承擔準政府職能。
主動去杠桿的積極成效有待解決的部分問題:從信用市場二元化到基建的過快回落。去杠桿取得了兩個顯著成效,一是金融去杠桿降低了部分金融產(chǎn)品的杠桿風險(資管新規(guī));二是實體去杠桿初步建立了地方舉債的增量規(guī)則(資管新規(guī)、隱性債務)。但在取得積極成效的同時,它也伴隨著一些問題:一是在金融去杠桿過程中,由于表外定價機制的缺失,高風險資產(chǎn)缺少風險識別和風險定價補償?shù)臋C制,貸款利率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一個最高限價,信用市場呈現(xiàn)出“二元化”的特征(我們在前期報告中一直在論述什么叫信用二元化,以及為何會出現(xiàn)信用市場二元化);二是在實體去杠桿過程中,全口徑基建增速從過去三年的15%一度下降到單月負增長。地方政府投資是地方增長的發(fā)動機,基建投資增速的過快回落帶來一系列連帶影響。
在貿(mào)易摩擦逐步升溫之后,這樣的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漂亮去杠桿的原則和政策的積極調(diào)整。達利奧(Ray Dalio)在Economic Principle中曾指出存在三種不同類型的去杠桿,其中“漂亮去杠桿”的要義是名義增長率高于名義利率,收入增長要高于債務。
在政策重心調(diào)整的背景下,中國去杠桿的政策逐步朝“漂亮去杠桿”調(diào)整和過渡。7月2日金融委會議使用“結(jié)構(gòu)性去杠桿”一詞,指出要“維護金融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以及“把握好監(jiān)管工作節(jié)奏和力度”。7月31日政治局會議指出經(jīng)濟運行“穩(wěn)中有變”,“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明顯變化”,指出要做好“穩(wěn)就業(yè)、穩(wěn)金融、穩(wěn)外貿(mào)、穩(wěn)外資、穩(wěn)投資、穩(wěn)預期”的工作。10月19日,劉鶴副總理講話指出,通過"毀滅性創(chuàng)新",中國經(jīng)濟中一些過剩領域的價格水平回歸均衡,供求關系明顯改善”,“下一步重點應是增強微觀主體的活力、韌性、創(chuàng)新力”。
我們估計這一趨勢在2019年,至少在2019年上半年將會是延續(xù)的。在上述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脈絡,一是金融和實體去杠桿中所伴隨的問題,最突出的是“信用二元化”和民企、中小企業(yè)融資難,以及相對于名義增長率來說基建的過低增長;二是貿(mào)易摩擦帶來的外部環(huán)境的明顯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六穩(wěn)”壓力。這兩個脈絡下的經(jīng)濟狀況仍目前沒有實質(zhì)性變化。所以我們估計從去杠桿向穩(wěn)杠桿轉(zhuǎn)變的趨勢,在2019年尤其是2019年上半年將會是延續(xù)的。
政策從去杠桿向穩(wěn)杠桿過渡所帶來的影響。政策從一輪集中去杠桿向穩(wěn)杠桿過渡,這會對資產(chǎn)定價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從總體上這一過程會降低風險資產(chǎn)的不確定性折價。如果去杠桿最終目標是快速出清,則經(jīng)濟會經(jīng)歷一輪陣痛,資產(chǎn)價格會包含明確折價。這一過程替代為穩(wěn)杠桿,則經(jīng)濟出現(xiàn)主動的、系統(tǒng)性調(diào)整的情形就會排除。
與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性出清關聯(lián)度最高的是高風險資產(chǎn),所以我們也一度看到高風險資產(chǎn)在政策調(diào)整后出現(xiàn)彈性更大的短期反應。
作者:郭磊 來源:華爾街新聞 責任編輯:jianping